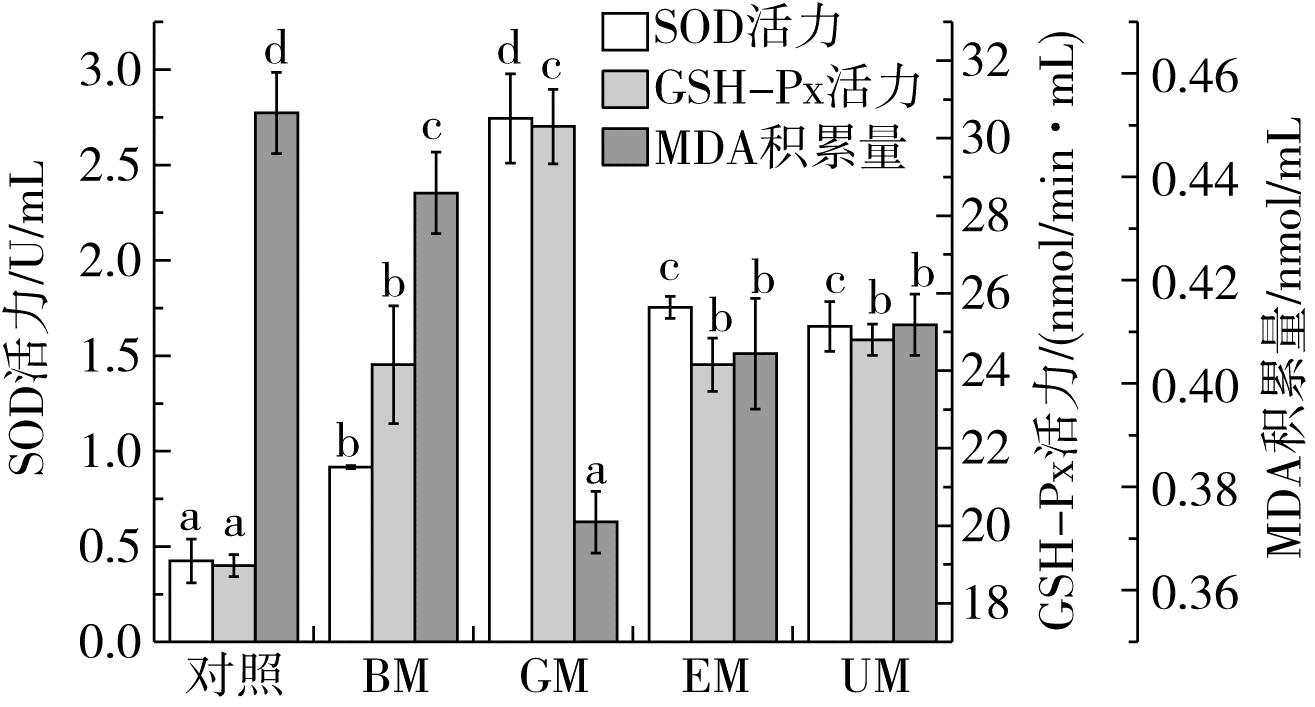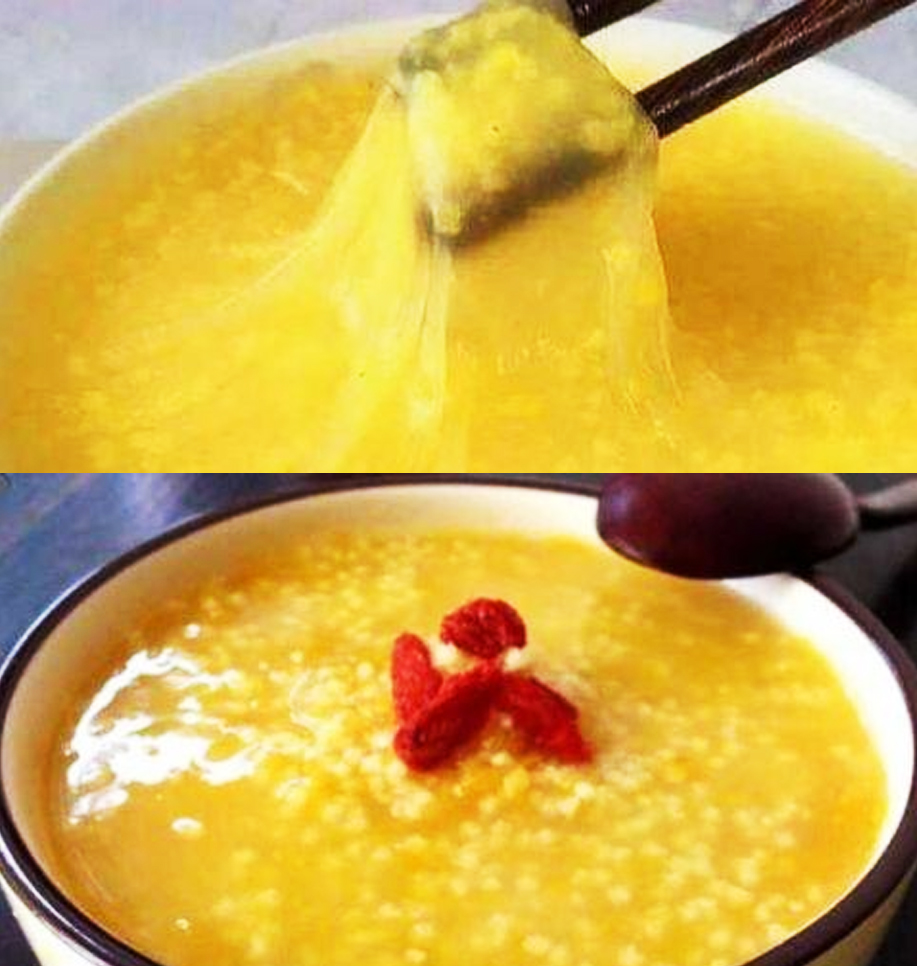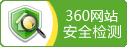▲绿油油的谷子地
又到一年打谷时。在我的印象中,打谷子是农村最难的一项农活。因为气温高,耗力大,每天干活持续时间长。
读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我年年参与打谷子,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。一次是14岁那年,我刚能熟练割谷子,就参加打面积9分多的沙田(田的名字,下同)。从上午10点一直干到下午1点钟,沙田还剩4分面积的谷子未打。阳光越来越毒,我闹着要马上回家,做饭吃,休息,下午再打。父亲却坚持打完才收工。他想趁着天晴、太阳大抓紧收谷子,尽量避开雨天,减少稻谷损失。趁着父亲挑谷子回家,我跑到树下躲太阳,喝茶水。远远看见父亲返来,我赶快去割谷子,割了半小时后,又跑到树下躲太阳,一歇气就是10多分钟,想以怠工方式逼父亲收工。可父亲只顾打谷子,我只得继续割谷子。等父亲再次挑谷子回去后,母亲和哥也停下来歇气、喝水,母亲喝了水后便去拴草。接下来,哥割上半小时也要歇上10分钟,我则最多割20分钟就要歇气。每有一点秋风吹来,那种一下从背心凉遍全身的感觉,我感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享受。就这样,我和哥轮番上阵;直到下午4点钟,我们终于打完了沙田的谷子。我感觉到身体轻飘飘的,世界有点在旋转;感觉到能坐在田坎上休息是无比的舒服。我很热,很累,可父亲和母亲呢,他们几乎没坐下来过,一直在烈日下剧烈劳作啊。这是我至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打谷子。

▲晒谷子
另一次是16岁那年打面积6分的弯田。快到12点了,弯田的谷子还剩2分未打完。我巴望着父亲吩咐收工。可广播一响,父亲却一点收工的迹象都没有。这时不远处来了两个父亲的朋友。他们走拢就下田帮打谷子,让父亲去挑谷子。他们身体魁梧,手又粗又黄又长,力气特大,拣谷把、脱谷粒、拴谷草,动作一气呵成,简直就是打谷子的机器。我拼命地抓紧割谷子,脸上汗如雨下,膝盖以上的衣裤被汗水反复浸透,小腿浸泡在泥水中。即便身处“水深火热”,我也不敢伸直腰轻松一下;我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:“快割!快割!”,两只手以最快速度割好一块块谷把;我感到自己似乎成了割谷子的机器。即使这样,原先割好的一大片谷把还是很快被他们打完;拌桶快速向我靠近,直至几乎抵着我的屁股,让我被拣了不少热谷把(刚割好就被人从手里抢去的谷把)。直到割完弯田的谷子,我才慢慢地直起腰,只觉得浑身湿漉漉,四周的景物有点模糊。这时,父亲许诺把另一块一分田的谷子打完就收工。我和哥赶快过去,一口气将整块田的谷子割完。从田里起来,刚过下午一点钟。我和哥的手指不知什么时候磨破了皮,还在流血;衣服上现出了一团团白花花的盐分——汗水流得实在太多了。这是我至今割谷子最快的一次,也是第一次磨破手指。从那以后,与我一起打谷子的人都说,我割谷子的速度长快了不少。
对我来说,“汗滴禾下土”和“粒粒皆辛苦”是感同身受的实践、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曾经的辛劳,比古人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(文 孙品才)